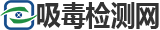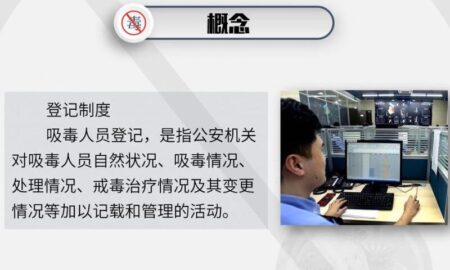戒毒人员在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的房间里。
“离开东莞!”
2013年7月22日,何志军告诉《南风窗》记者,自愿戒毒者出院后,这是他反复给他们的第一条建议。
何志军是广东惠州市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院长。他们医院每年接纳的自愿戒毒者有1500人,其中60%来自东莞。“不能说,东莞就是吸毒贩毒最泛滥的地区,但统计结果就是这么个比例。”
最近几年,珠三角患者以吸摇头丸、K粉、冰毒等新型毒品为主,吸白粉已是很少了,但来自东莞的患者中,总能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吸白粉的,且是最近一两年才吸的。
吸毒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最小吸毒者竟然只有14岁,这是何志军感受到的“最悲哀,也是最无力的事情”。
自愿戒毒的概念,从提出到在争议中的实践,走过了10多年。吸毒者也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犯人”,变成了医学领域上的“病人”,但问题总是不断地产生。
制 度
过去吸毒者一旦被抓,一般不会受到很好对待,然后被扔进“牢房”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吸毒者享受到的总是这样的“待遇”。渐渐地,人们也习惯于将吸毒者和犯人划上了等号。
针对这些吸毒者,过去几十年里,传统的戒毒方式主要有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强制戒毒属公安系统管,劳教戒毒属司法系统管。吸毒者被公安机关抓到后,先关3个月进行强制戒毒,期满后再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劳教戒毒—时间通常是2至3年。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08年5月底。6月1日后,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取消了劳教戒毒。当下主要的戒毒方式变成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其中,自愿戒毒被排在第一位,此时,传统的戒毒方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西方很多国家,甚至是港澳地区,是没有强制戒毒的,自愿戒毒一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流行的戒毒方式。不过,一直到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才提出自愿戒毒的概念。此后,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药用滥用防治学会上,来自学术界、公安系统和政府官员的论争,非常激烈,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担心毒品流入医院,二是对医院管理不放心。
现在看来,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和公安的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不一样,自愿戒毒医院是民间资本投入的,没有官方资金补助。即使出于投资回报考量,正常的经营者是不愿让毒品流入医院的。
后来,国家也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在2011年6月26日施行的《禁毒条例》中明晰,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相反,如果吸毒人员因被公安机关抓捕,而进行强制隔离戒毒,会留有案底。一开始,很多吸毒者以为这些医院是和公安机关联网的,所以有些顾虑。事实上,如果他们到自愿戒毒医院戒毒,包括他们的隐私在内,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花 样
到医院戒毒的人,内心是矛盾的:他们既想戒掉毒品,又担心戒不掉,自己因此会很难受。所以,他们偷偷将毒品带入医院,以防受不了时,吸上两口。
为将这些毒品带入医院,吸毒者的手段五花八门:有将鞋子割出一条缝,然后把毒品放在里头粘好,混入治疗区;有通过朋友送饭、送饮料等方式,将毒品放在汤底或饮料内混入。
“有个患者叫他奶奶拿饮料来给他。按常理,奶奶怎么会给孙子送毒品?”何志军说,但检查中发现,饮料中确有毒品。
原来,患者来戒毒前,就已把饮料弄好放在家里的冰箱,然后才叫他奶奶送来的,他奶奶对此并不知情。
戒毒人员进入医院戒毒时,需经过严格检查,这包括:梳头发、换鞋子、看衣领衣角,检查手机。另外,患者得全身脱光并做“起立蹲”的动作。
为将毒品带入医院,患者经常在口香糖里粘点白粉,后将口香糖粘到自己发根;或者将手机撬开,在手机夹缝或充电器与手机间,压些毒品在里头;有的甚至将毒品塞进屁眼里—医院让患者脱光衣服并做“起立蹲”动作,目的就是避免毒品借此渠道流入医院。
更绝的是,还有通过遥控直升飞机将毒品遥控到患者居住的窗口,或通过弹弓或橡皮筋等方式将毒品弹到患者住地。
不过,因医院有监控,所以这些手法难以得逞。
奇怪的是,自愿戒毒医院里的患者,也不都是真心来戒毒的,他们的想法颇多。这种想法演变成了行动,使一所所戒毒医院都成了一个个的江湖。
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副院长夏鄂州告诉《南风窗》记者,医院里的戒毒者,除了真心想戒毒的人之外,还有另外四类人:一是避风头的。如果外面严抓吸毒、贩毒,吸毒者就跑到自愿戒毒医院戒毒,等风头过再出来。因为,一旦在外被公安机关抓住强制隔离戒毒,一关就是两三年,他们不愿意受那份苦。二是调养身体。长期吸毒对身体不好,特别是冰毒等新型毒品,其毒性远比传统毒品强,对身体的伤害更大。到戒毒医院戒毒的一些人,有的根本不缺吸毒的钱,主要想借此调养自己的身体,出去了,他们还会吸。三是为了节约费用。吸毒者中,吸得较多的,每天消费600元至800元。如果经济不是很宽裕,在外面一个月消费2万元左右,但进入戒毒医院戒毒,一个月几千块钱(哪怕是1万多元),这些费用相对于在外面的花销,是要少很多。四是以贩毒为目的。这类人想方设法把毒品弄进来,以高价卖给戒毒人员。此外,他们互相串门、要电话等,希望出去后有业务联系。
如果出现以贩毒为目的的戒毒方式,医院通常会给派出所报案。但如果证据不足,而对方又不服从管理,医院也只好让其出院。同时,戒毒医院规定戒毒者彼此之间不能互相串门,不能留彼此的电话。
吸毒者
在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戒毒的阿东,很少出门,整天呆在房里。阿东是东莞市大朗镇的一名自愿戒毒者,今年20岁,吸白粉有一年的时间了。
阿东本是大朗镇一所中学的高中生,染上毒瘾后,他没法继续读书。吸毒后,他每天的生活变成了“找钱—吸毒—再找钱—再吸毒”。如此往复。
为找钱,很多吸毒者最终走上这样的路子:首先是骗,骗不了就去偷。偷不成,就去抢。抢不了,就去贩毒,以贩养吸,甚至闹出了人命—这是很多吸毒男子的人生轨迹。女吸毒者,通常沦为卖淫女。他们整天就琢磨两件事—找钱、吸毒。人生几乎和社会完全脱节。阿东不希望如此,吸毒后,他尝试做了一个月的工作,但“很难受,毒瘾发作时,浑身没力,流鼻涕、胸闷”。
吸毒者有两种人格:毒瘾来时,是一种人格。吸毒后,又是另一种人格。这种分裂,住在阿东隔壁的阿平体验最深。阿平并非“瘾者”,他这次是陪他老婆阿秀来戒毒的。“我老婆毒瘾发作时,连杀人都能干出来的样子。那一刻,我感觉她很陌生。”阿平说,但她搞完(吸毒)后,又很后悔。
阿平和阿秀是一对年仅30岁的夫妇,老家在湖南郴州。他们长期在东莞中堂打工。两年前,阿秀在中堂君湟酒店KTV和朋友玩时,染上了毒瘾。阿秀说,“君湟KTV里的毒品就像点菜、卖酒一样,服务员拿着个托盘问你要什么。”
不过,这个酒店今年5月被东莞特警突袭。酒店里,包括吸毒人员、服务员、保安在内的2000余人,都被带走。此后,在东莞常平等地酒店,警方也带走了大批吸毒者—这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广州交警某中队副队长邱某。
“都怪自己贪玩,去唱K,大家一起疯,结果就这样了。”阿秀说,开始只是好奇,朋友叫她试试,说不是白粉,是蓝精灵,不会上瘾。事实是,朋友骗了她,而她的好奇心让骗局得逞。
闲聊时,阿秀用手用力地揪自己腿部和心脏,说“酸痛,好难受,感觉像成千上万只蚂蚁在身体里不断爬着、撕咬着”。阿平后来喊来了医生,医生给她注射一针后,情况才好转。
阿秀说,如果当初知道是白粉,肯定不吸了。持这样观点的,还有阿东。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白粉进行大量宣传,很多人对白粉的危害是有清醒的认识和警惕。但东莞,还有大量吸毒者吸白粉。这是因为在营销上,贩毒者包装并玩起了新概念。“比如他们吸的‘伍仔’,医学上没这个概念。”何志军说,检测发现,所谓的“伍仔”就是“白粉”。
贩毒者为引诱他人吸毒,常避免使用白粉、鸦片等字眼,他们习惯于用“伍仔”、“蓝精灵”、“神仙水”等比较新鲜时尚的概念去包装。
事实上,这些东西不是传统毒品—白粉,就是K粉、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其危害性同样非常巨大。对喜欢玩、好奇、乐于尝鲜的人来说,这是容易陷进去的。阿秀说,她在中堂君湟酒店KTV玩时,发现很多初中生、高中生也在吸这些东西。
贩毒的人,一开始都很大方地免费提供给新人吸。等对方上瘾了,贩毒者就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将吸毒者乃至其家庭的全部财富源源不断地吸入自己口袋,直至吸毒者的全部财富被抽干。
医 院
经过自愿戒毒医院治疗后,一些意志坚定的患者,可以戒掉毒瘾,但更多的人无法戒掉,他们反反复复地进出这些医院。这种反反复复,让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也没有成就感。
广州白云自愿戒毒医院业务副院长邓雪峰告诉《南风窗》记者,“戒毒治疗不像外科,动个手术,病人很快恢复了,还很感谢你。”戒毒医院的情形是:患者刚出院几天,又回来了!有的甚至进出医院四五十次,成了医院的常客了。这种挫败感,时常让医护人员感到无力。
而看不到前途,没有多大发展空间,也在困扰着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吸毒属于药物滥用—这有点偏门,人才难招。而在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上,卫生部在这领域没有专门的诊疗科目。
因为药物滥用是被纳入精神科下面的一个分支,但它和精神科又有很大的差别。从事戒毒治疗工作的,实践中,它和精神科是有很大脱节的,所以在职称评定中,自愿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优势,也很难获得职称上的提升。所以一些医护人员不愿意在这个领域继续干下去,因为担心职业选择会越走越窄。
吸毒者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很高,医护人员经常和他们接触,危险系数也增高。而长期吸毒的人,在人格上是有分裂的,他们对医护人员的态度较蛮横,甚至是故意刁难。
上述种种因素,都在加剧这个行业的人才流失。以广州白云自愿戒毒医院为例,医护人员每年流失率达40%,最高时,流失率达50%。
另外,这些自愿戒毒医院没有财政拨款,行业的生存还是比较艰难。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约有40多家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疗服务。但目前,整个广东的戒毒医院只有4家,其他的戒毒科、所大概13家,总共加起来就剩17家了。以惠州为例,以前有6家机构,目前只剩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一家了。
因为投入比较大,多年来,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一直是负数经营。之所以还在坚持,是因为老板想把这个医院当做一个品牌来经营。这家戒毒医院的老板是惠州一家很大的房地产商。
何志军说,老板对他讲不要有经营压力,“我搞房地产,一年卖几十万平方米,我一平方米多卖5块钱就都回来了,你不要考虑挣钱,专心打品牌就是”。
但更多从事戒毒的医院,就不能这么洒脱了。在自愿戒毒医院数量由鼎盛走向萎缩时,吸毒人员却不断上升—“官方说有220万人在吸毒,那主要是在公安系统留有案底的,如果包括自愿戒毒的群体,估计超过1000万。”

戒毒人员在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的房间里。
“离开东莞!”
2013年7月22日,何志军告诉《南风窗》记者,自愿戒毒者出院后,这是他反复给他们的第一条建议。
何志军是广东惠州市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院长。他们医院每年接纳的自愿戒毒者有1500人,其中60%来自东莞。“不能说,东莞就是吸毒贩毒最泛滥的地区,但统计结果就是这么个比例。”
最近几年,珠三角患者以吸摇头丸、K粉、冰毒等新型毒品为主,吸白粉已是很少了,但来自东莞的患者中,总能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吸白粉的,且是最近一两年才吸的。
吸毒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最小吸毒者竟然只有14岁,这是何志军感受到的“最悲哀,也是最无力的事情”。
自愿戒毒的概念,从提出到在争议中的实践,走过了10多年。吸毒者也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犯人”,变成了医学领域上的“病人”,但问题总是不断地产生。
制 度
过去吸毒者一旦被抓,一般不会受到很好对待,然后被扔进“牢房”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吸毒者享受到的总是这样的“待遇”。渐渐地,人们也习惯于将吸毒者和犯人划上了等号。
针对这些吸毒者,过去几十年里,传统的戒毒方式主要有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强制戒毒属公安系统管,劳教戒毒属司法系统管。吸毒者被公安机关抓到后,先关3个月进行强制戒毒,期满后再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劳教戒毒—时间通常是2至3年。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08年5月底。6月1日后,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取消了劳教戒毒。当下主要的戒毒方式变成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其中,自愿戒毒被排在第一位,此时,传统的戒毒方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西方很多国家,甚至是港澳地区,是没有强制戒毒的,自愿戒毒一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流行的戒毒方式。不过,一直到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才提出自愿戒毒的概念。此后,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药用滥用防治学会上,来自学术界、公安系统和政府官员的论争,非常激烈,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担心毒品流入医院,二是对医院管理不放心。
现在看来,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和公安的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不一样,自愿戒毒医院是民间资本投入的,没有官方资金补助。即使出于投资回报考量,正常的经营者是不愿让毒品流入医院的。
后来,国家也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在2011年6月26日施行的《禁毒条例》中明晰,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相反,如果吸毒人员因被公安机关抓捕,而进行强制隔离戒毒,会留有案底。一开始,很多吸毒者以为这些医院是和公安机关联网的,所以有些顾虑。事实上,如果他们到自愿戒毒医院戒毒,包括他们的隐私在内,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
自愿戒毒医院的涌现,没有引发公安系统方面当初担心的严重问题。不过,医院方面也发现,在和自愿戒毒者打交道时,问题的复杂性也高于医院当初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