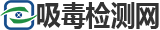毒品犯罪中“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具体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对毒品犯罪中“以贩卖为目的”的判断要摆脱传统的“供有则有、供无则无”的口供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坚持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证书证到言词证据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审查,以查证属实的“非法购买”这一基础事实和毒品的数量、贩卖所用工具等相关证据推定行为人“贩卖目的”的存在。在行为人没有明确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对推定事实构成合理怀疑时,可以认定其具有“贩卖目的”,进而构成贩卖毒品罪。
[基本案情]2012年11月7日中午1时许,刘某以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从黄某处购得冰毒896.4克,存放于其承租的房屋内。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发现之后,于当日下午5时许将正要外出的刘某抓获,当场从其身上查获冰毒一袋,净重49.6克。随后,民警对刘某租赁的房屋进行搜查,在卧室的衣柜内查获用透明塑料封口袋包装的冰毒17袋(每袋重量为49.5克到50克不等,连同从其身上查获的冰毒共计896.4克),并从其卧室内查获电子秤2台、封锁机1台、透明密封塑料口袋40多个、手机2部等物品。刘某辩称,购买冰毒是为了吸食,将冰毒分成重量基本相同的18小袋进行包装是为了方便携带,购买电子秤是为了在买菜后方便称重,封锁机是朋友暂时存放在其租赁房的。
一、分歧意见
对于该案犯罪嫌疑人刘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理由是刘某在供述中称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没有贩卖毒品的前科,在购买毒品后没有贩卖行为,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主观上具有“贩卖目的”。因此,不能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刘某明知是毒品且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非法持有,数量已达到我国刑法第348条所规定的追诉标准,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
第二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刘某购买的毒品数量远远超出了其吸食的剂量,并且从其家中查获电子秤2台、封锁机1台、透明密封塑料口袋40多个。在检察机关承办人对其电子秤、封锁机、透明塑料袋的用途进行讯问时,刘某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为刘某称电子秤是为了买菜做饭时核对菜的重量,但在其承租的房屋内没有厨具,邻居证实没见过有人住,房东证实天然气表的数字和在将房屋出租给刘某时相差无几;追问刘某哪个朋友将封锁机放置在其承租屋时,刘某无法提供该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因此,应推定刘某具有“贩卖目的”,刘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二、法理释评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刘某主观上是否具有“贩卖目的”,因为根据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2012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1条之规定,“‘贩卖’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如果认定刘某主观上具有“贩卖目的”,则应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反之,则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认为,从刘某的客观行为来看,应当认定刘某主观上具有“贩卖目的”,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前提性的澄清
对本案进行释评之前,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贩卖目的”是否要求有相应的客观行为与之相对应。因为第一种观点认为,证明刘某主观上具有“贩卖目的”的情形之一就是刘某在购买毒品后实施了贩卖行为。对于多数的故意犯罪而言,故意的内容与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具有对应性,即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规制着故意的内容。“但是,目的犯中的目的、倾向犯中的内心倾向、表现犯中的内心经过(心理过程),则不要求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只要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即可。”[1]它是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虽然“贩卖目的”的实现,需要行为人在非法收买毒品之后再实施贩卖行为,但是根据《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1条关于“贩卖”含义的界定,只要行为人以实施贩卖为目的而实施了非法购买行为,就以犯罪(既遂)论处,而不需要行为人在实施非法购买毒品的行为之后再实施贩卖行为。[2]这种目的犯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短缩的二行为犯”,即“‘完整’的犯罪行为原本由两个行为组成,但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以实施第二个行为为目的实施了第一个行为(即短缩的二行为犯的实行行为),就以犯罪(既遂)论处,而不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第二个行为;与此同时,如果行为人不以实施第二个行为为目的,即使客观上实施了第一个行为,也不成立犯罪(或仅成立其他犯罪)。”[3] 因此,第一种观点中以刘某在实施非法购买行为之后进而再实施贩卖行为来判断其主观上的贩卖目的是不可取的,该种做法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与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理论相悖。
(二)认定主观事实的逻辑与方法
“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中的“贩卖目的”是一种主观要素或者事实,它不像客观事实那样可以通过人类感官直接感知或认知,而是“需要通过其他的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并依靠推论(推定)的方法加以辅助显现。”[4]主观事实的认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但困扰着我国大陆的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同时也困扰着域外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司法者,对其认定需要经过外部资料进行判断已成为共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深藏于内心的主观事实,不像外表的行为可以直接看见,并直接表述于审判者面前,他人无从窥见其内心,只有从其他情况事实,间接地推论方可得知。”[5]德国学者指出,“在查明故意、特定意图和动机等心理要素时会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只有从外部事实及心理学上法则进行必要的反推,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6]我们认为,对案件主观事实的认定,从逻辑上来说,需要摆脱以口供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建立起一种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证书证到言词证据的逻辑思维;从具体方法上来说,需要合理运用刑事推定原则。
1.审查案件证据的逻辑思维。司法者需要形成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证书证到言词证据、从外围证据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的逻辑思维过程。打破传统的口供为先、以口供为中心、从供到证的思维范式,杜绝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来认定案件的主观事实。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优于言词证据。因为言词证据具有可变、难以固定的特性,“对于每一个提供言词证据的人,随着时间、地点和提取的人的不同,言词证据的内容都有可能发生变化。”[7]特别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很少承认自己的真实意图,为逃避法律的惩罚而百般辩解成为其第一选择。与言词证据相比,物证、书证则以客观存在的实物及其反映形象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物证不会因为证人的存在而缺席。物证不会发生错误。物证不会作伪证,只有物证的解释才可能出现错误。”[8]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说,遵从从客观到主观、从书证物证到言词证据、从证到供的证据审查逻辑,符合人类的认知图式,有利于司法人员客观公正地查明案件事实,是对新刑诉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贯彻落实。因为这种审查逻辑是对口供中心主义的超越,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2.认定案件主观事实的具体方法运用。主观事实因深藏于行为人的内心而难以认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难以认定不等于不能认定,因为主观事实在具备主观性特征的同时也具备客观性的特征,即人的主观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它不是纯粹的主观自生的事物,而且,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会通过其客观行为外向化、客观化。这便为化解刑事主观事实证明的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即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的主观事实时,应当全面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以及与行为相关的因素,综合分析全案证据,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反推其主观心理态度,科学合理地运用刑事推定原则。
刑事推定是诉讼中一种重要的事实认定方法和司法证明方法,是指“裁判者根据已经得到证明的基础事实,认定存在推定事实。”[9]它是解决主观事实证明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虽然说刑事推定不是主观臆断,更不是有罪推定,[10]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事实推定,是一种相对的证明而不是绝对的认知判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冲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必须严格限制。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用作推定依据的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且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常态联系”。基础事实真实可靠,是指基础事实得到证据的证明,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是指“当基础事实存在时,推定事实也存在的概率极高,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近似于充分条件的逻辑关系。”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或然性联系,而非必然性联系。”[11]二是在证明标准上,无论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还是对处于反驳立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证明标准只要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无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因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们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且举证能力有限,要求其反驳的证明标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会增加他们提出辩护的门槛、降低成功的几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设置和运用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转移证明责任来缓释严格证明的难度,如果要求其证明标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那么刑事推定的存在基础就会荡然无存。[12]三是必须设置反驳程序,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权。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的反驳具有具体明确的证据支撑或可调查的证据线索,经查证属实后构成对推定事实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应当否定推定事实的存在。
(三)回归到本案的具体分析
依照上述我们所提倡的审查案件证据的逻辑思维,对本案证据进行审查便应当从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房屋租赁合同、毒品称重记录、手机通话清单、尿液检测报告书、毒品检验报告等物证和书证开始,再到刘某承租房的邻居、房东以及同案人黄某等人的证言,最后再看犯罪嫌疑人刘某的供述。尿液检测报告书证明刘某系吸毒人员,其与其他物证书证可以联合证明刘某明知是毒品而非法购买持有这一事实,同案人黄某的指证则进一步印证了该事实。据此,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已不存在疑问。这一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过程,是对传统的“供有则有,供无则无”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超越,有效地摆脱了单一依靠口供这一直接证据认定事实的模式及其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的弊端,坚守了证据裁判原则。当然,对于本案来说,进行到这一步还没有完结,因为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中,行为人都会非法持有毒品,只有在犯罪分子拒不供认,又无证据认定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窝藏毒品罪中任何一种罪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这就需要综合审查案件证据,对刘某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即判断刘某的行为是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还是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窝藏毒品罪中的其他犯罪。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于“贩卖”含义的界定可知,如果刘某具有“贩卖目的”,则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而对刘某是否具有“贩卖目的”的判断需要科学合理地运用刑事推定原则。
对于刑事推定原则运用时应当把握的三个方面,前已述及,不再赘述。结合本案来说,首先,本案的基础事实是刘某非法收买毒品,这一事实已经得到案件现有证据的证明,且已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并且,非法收买毒品这一基础事实和我们所要推定的贩卖毒品这一事实存在着“高度盖然性的或然性联系”。因为对于购买大量毒品的人来说,供自己吸食的可能性较小,购买之后往往是为了贩卖。其次,在证明标准上,对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即对刘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判断是基于其非法收买行为而进行的推定,并不要求刘某客观上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在证据的把握上也就不要求有交易毒品的毒资、购买人的证言等证明刘某实施了贩卖行为的证据。对于刘某反驳证据的把握同样如此,如果刘某对其贩卖事实即“贩卖目的”的反驳具有证据支撑,便可否认推定的贩卖事实的存在。所谓的反驳事实比如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电子秤、封锁机、塑料袋等不是其本人所有或另有用途等。再次,设置反驳程序就是对案件进行审查时,司法人员需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用推定的事实对刘某进行讯问。如果刘某的反驳具有证据支撑或可调查的证据线索,且经查证属实后构成对推定事实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应当否定推定事实的存在,只能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刘某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支撑其反驳,或者其无法对司法人员针对推定事实提出的问题做出合理解释,那么就应当认定推定事实成立,即刘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中,均称购买冰毒是为了吸食,否认其“贩卖目的”的存在。检察机关承办人在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刘某进行讯问时,问刘某购买毒品的用途,刘某依然坚称是为了吸食,承办人便抓住现有证据继续对其发问,问其在社区是吃低保的人从何处拿来20万元人民币,吃低保怎么还一次性的花费20万元来购买毒品,每天吸食毒品的剂量,从其租赁的房屋搜出的电子秤、封锁机、40多个透明塑料封口袋的所有人、用途,为何将冰毒分成重量基本相同的18小袋。刘某辩称20万元是之前做生意存下来的,但这一辩解被之后对其银行账户的查询和其妻子的证言所否定;刘某现年57岁,其购买如此多的毒品用来吸食要吸食多长时间?这显然不合常理;其辩解电子秤用途是核对做饭买菜时菜的重量,但被房东提供的自刘某承租后天然气的用量几乎未动和邻居从未见到刘某买菜以及在房屋内并未搜查出饭锅、碗筷等做饭用具这些事实所推翻;其称封锁机是朋友存放在租赁房屋,但在承办人问其朋友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时无法回答;其称透明塑料封口袋是当天为分装毒品时买多了,但其提供的购买透明塑料封口袋的地址经查系虚构;其辩称分装成18小袋是方便吸食时携带,但不可能一次性吸食40多克,也不必分装成重量基本相同的小袋。据此,我们认为应推定刘某主观上具有“贩卖目的”,其针对主观上没有贩卖目的的反驳不成立。
三、余论
本案推定刘某主观上具有“贩卖目的”,进而认定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不但具有学理上的支撑,同时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正如学者所言,刑事诉讼法的该条规定为化解主观事实的证明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开了一扇窗。[13]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
[2]对于司法实践中将“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既遂的作法,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种行为应当作为犯罪预备或非法持有毒品罪来认定。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7页。
[3]张明楷:《论短缩的二行为犯》,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148页。
[4]高铭暄、孙道萃:《论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的认定》,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2期。
[5]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22页。
[6][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7]张军:《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8][美]威廉·奇泽姆等:《犯罪重建》,刘静坤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9]樊崇义、吴光升:《论犯罪目的之推定与推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0]张旭、张曙:《也论刑事推定》,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1]张云鹏:《刑事推定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页。
[12]孙道萃、黄帅燕:《刑事主观事实的证明问题初探》,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5期。
[1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