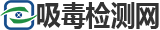富二代喝止咳水上瘾 父母深山建房圈禁逼其戒毒

饭后,罗伟在农舍门前点燃了一支烟。

河源深山里,罗伟住了8个月的农舍。

面对止咳药水的诱惑,24岁的罗伟无法抵挡。父母将他丢入河源农村9个月的隔离,让他逐渐摆脱成瘾的梦魇。这样的自救也吸引了不少深圳成瘾者家庭效仿。与世隔绝始终是权宜之计,回去还会不会再喝?罗伟也没有把握。身瘾易戒,心瘾难治。
被隔离的青年
“割草、喂鱼、扫地还有浇菜。”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在山里的生活,由于甚少与外界联系,罗伟的手机坏了都懒得去修。
24岁的罗伟,拥有让很多同龄人艳羡的身份:深圳原住民、富二代。依靠收租,他所在的家庭拥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
但罗伟已经在河源的偏远村落的一栋危房里生活了九个月。他被父母圈禁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目的只有一个,远离止咳水。
罗伟现在的生活简单而枯燥。早上8点,罗伟的一天从割几十斤鱼草开始。之后,他还要花几个小时,给自己种的青菜浇水,然后打扫舅舅家的房间和走廊。如果有空,他喜欢到附近的村民家里坐坐,聊聊天喝喝酒。晚上,他也偶尔看电视,但更多时候是晚上10点就睡觉了。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罗伟,从未干过此等粗活。“割草、喂鱼、扫地还有浇菜。”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在山里的生活,由于甚少与外界联系,罗伟的手机坏了都懒得去修。
他有些习惯现在的简单生活,但对于回到不算遥远的深圳,他依然流露出向往。没有父母的许可,他寸步难行,即使到最近的县城,也需要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更重要的是,村里的长辈对他严格看管。
罗伟是深圳这座城市改革发展受益最大的“深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在学生时代,他每月都能获得数千元的零花钱。但不幸的是,罗伟沾上了坏习气,恋上了止咳水,在致瘾最深的时段,他每天能喝掉十瓶止咳水。
由于止咳水含有的化学成分,能刺激中枢神经,一次大剂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在深圳,一些年轻人滥饮止咳水的现象一直存在。
据罗伟回忆,他第一次接触止咳药水,是在深圳读中专时,他将沾染恶习的原因归结于所处的环境:“像我们这样的差学校,这东西很泛滥,一个班20个同学全是男孩子,只有6、7个人不碰(止咳药水)。老师也不管,每天不用读书,无所事事。”那一年他14岁,在此后的10年时间,止咳药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那间售卖止咳水的小店,就在他上学、放学的半路上,他承认,十年间自己无数次试图戒“水”,但自己抵抗诱惑的能力太差。
喝得最厉害的时候,罗伟一天就要喝掉10瓶咳嗽水,通常的剂量是一口半瓶。为了缓解喝止咳水之后的口渴,他每天还要喝掉5到6瓶1 .2升的可乐。由于水肿,身高1.6米的他,一度体重飙升到170斤。
邻居看不惯,”他们会和罗伟的父母说‘你儿子好像不太听话’,这句话已经说明了很多。”罗伟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街坊的批评,给父母以及自己很大的压力,感觉自己在社区就是个瘾君子。
深感这样下去不行的罗伟和家人,开始寻找新的解决的方法。
家长的救赎行动
面对逐步好转的儿子,不差钱的罗全,又有了升级版的隔离计划:在山林的更深处盖一栋小平房,专门给儿子用作隔离屋,让儿子在此再调养一年。
钱就在口袋里,药水就在小店里,脱离不了环境,要戒瘾似无可能。
2011年的中秋节,忍无可忍的罗全,终于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救儿子:几天后,罗伟被送到河源农村,一个距离最近县城也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两个小时步行山路的小村落。
这里是一处罗伟舅舅承包的山林,蜿蜒曲折的山路阻止了外界的喧嚣,少有人为开发。尽管珠三角发展日新月异,但这片山林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模样。罗伟居住的小平房,还是上世纪60年代知青修建的瓦房。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罗伟的父亲罗全对记者说,这个地方他很满意:“他买不到止咳药水。”
刚开始的时候,罗伟并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开始的三四个月觉得很不适应,身体和心理的都有。那段时间老是发脾气。”
在此期间,不堪寂寞的罗伟曾经回深圳住了三个多月,很快,自认无法摆脱“心瘾”的罗伟,在半被迫半自愿的情况下再次回到这个远离城市的深山老林里。
山里没有多少劳作事,罗伟也不需要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但舅舅定下了强制性的规定,在罗伟眼中,舅舅是一个强势的人。
“比较懒,不干事,骂啊,不骂不行。”叶伟华这样评价自己的外甥:“要经常说他,跟他讲人生道理,总之在这就不能给他主动权了。”谈话中,叶伟华避着止咳药水四个字,以“那东西”指代,认为不是什么好东西。
经过9个月的隔离生活,让罗伟的身体状况好了很多,170斤体重减到了130斤,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一边是亲人热心安置,另一边是要早点跑出去的心。“在山里8个月,我想回去,其实我每一天都想回深圳。”罗伟没有跟父亲提起过这种想法。
面对逐步好转的儿子,不差钱的罗全又有了升级版的隔离计划:在山林的更深处盖一栋小平房,专门给儿子用作隔离屋,让儿子在此再调养一年。
对于罗全的计划,靠近这个家庭的另外一个家庭也非常感兴趣,已明确表示要参与进来,这个家庭的一个年轻人,同样深陷止咳药水之瘾不能自拔。
在河源市连平县元善镇的深山里建一所房子,让罗伟在山里至少再住上一到两年,这样的房子大约花费30万。这对于罗伟家族来说,钱完全不是问题。据记者了解,这个家族属深圳原住民,在城市核心区拥有大量出租屋,用罗伟的话说,只要不胡乱挥霍,父母攒下的积蓄,所有家庭成员一辈子都花不完。
10月30日上午,罗全驱车四小时来到连平县元善镇仙塘下林场,午饭后,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山路进山选定了建房子的地点。“不要建得太好,但一定要快,最好12月就能住上。”
8是个吉利数字,但11月8日皇历显示“诸事不宜”,罗全选择11月7日破土动工建房子。
无论是选址半山腰盖房子,还是去留问题,罗伟都没有任何发言权,他悄悄对记者说,自己不想呆在山里。
罗伟要了根烟,蹲在一边看着父亲和叶伟华忙碌地指挥工人。砂石、钢筋和水泥都齐备了,加上当地高效率的师傅和小工,眼前这个专门为自己建的房子在12月中旬就可以完工了。
成瘾者家庭的希望
走投无路之际,陈玲听到了罗伟隔离戒瘾小有成效的事,便找到罗全商议把儿子也放到山里面。“出钱建个房子,让他呆在一个完全没有止咳药水的环境里。”
罗伟在河源的大山里过上正常生活,这件事在他宝安的生活圈子里得到传播,附近的几个同样被止咳药水伤害着的家庭上门拜访,请教自救方法。
长期关注止咳水问题的深圳市点点青少年药物成瘾关爱中心,也注意到了罗伟家庭的隔离计划,在中心的牵线下,一些成瘾者家庭也开始热切地观望,待隔离屋修建完毕,且隔离效果良好,他们会考虑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去。
“医院治疗无效,戒毒所不收,就算收了也要留案底,前些天送到东莞一精神病院了,不指望能戒断,希望情况好转时接到河源。”陈玲是罗全的邻居,9月底将喝止咳药水成瘾的儿子送到精神病院。
沾染止咳药水之前,陈玲的儿子就读于宝安某重点中学。高二时老师告知儿子在课堂表现不正常,成绩也大幅下滑。于是陈玲开始跟踪儿子,发现一向优秀懂事的儿子喝上了止咳药水。
“成瘾后就完全变了个人,脾气非常暴躁,经常变着法子要钱,不给钱,他就动手打人,有一回竟然上来掐住我的脖子,可怕得像魔鬼一样。”为了帮儿子戒断药瘾,陈玲进行了长达5年的抗争,但丝毫不见起色,“最近一次到医院是去年五一,治疗了两个月,回来没几天又复喝了。”
罗全也认为,周遭恶劣的环境,是众多小孩喝止咳水上瘾的根本原因。他家所住小区,30多户人家中有10来个小孩喝着止咳药水。“周围都是喝止咳药水的小孩,卖药的竟然像点快餐一样,还可以送货上门。”
走投无路之际,陈玲听到了罗伟隔离戒瘾小有成效的事,便找到罗全商议把儿子也放到山里面。“出钱建个房子,让他呆在一个完全没有止咳药水的环境里。”11月7日,陈玲也出现在仙塘下林场的工地上,儿子还在东莞的精神病院呆着。这个决定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吗?“不敢告诉他,如果他知道了肯定是不愿意的。一出院就强制送进来。”
无奈的自救之路
河源的大山成为他们最后的希望。12月中旬是罗全他们计划的新房入住时间,罗伟将迎来目前呆在精神病院的病友。
如果是常规的路径,罗全和陈玲会把小孩交给社会,在公立或私立的医院,在政府主导的专门机构或民间组织中,而非精神病院或戒毒所,更没想过要走一条“上山下乡”的自救之路。“当外界所能提供的方案都无效时,只能自己搞自己的,实在没有办法了。”罗全对社会上的方案失望了。
“目前对止咳药水成瘾治疗的方法是以药物治疗为主,辅助康复治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在深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贾少微被视为治疗药物成瘾,包括喝止咳药水成瘾的权威,当深圳家长要把成瘾的小孩送医院治疗时,大多数选择送到他所在的核医学科。
“这是一个综合治疗的过程,除了积极进行医疗外,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密切配合,不仅要使止咳药水成瘾者停止滥用的行为,还要摆脱心理依赖,防止复喝”。贾少微说。
贾少微所在的科室,每天都有喝止咳药水上瘾的患者上门求诊,原因是深圳喝止咳药水上瘾的人特别多。11月13日上午,在诊疗室诊疗了最后一位成瘾患者后,贾少微接受了南都的采访。
当南都记者问及具体的治疗手段时,他回避了,一直强调通过治疗前后脑部CT扫描影像,能够证明其方法的有效性。罗全和陈玲都曾将儿子送到贾少微处治疗,医生充满自信,但患者并未康复。
对于成瘾者家庭来说,医院治疗的失败,意味着他们只能向戒毒所求援,但戒毒所不收喝止咳药水成瘾的患者,患者本身也不愿意在戒毒所留下案底。
“如果民间有什么人或组织敢收治这些成瘾的孩子,有关部门马上就会找上门,因为这确实是触犯现行法规的。”周丽辉说。周是中国首家止咳药水成瘾治疗公益机构 深圳市点点青少年药物成瘾关爱中心的创办者。至于违反具体什么法规,周丽辉不知道,但经常跟公安、戒毒所等部门打交道的她知道这事不能碰。“无奈的家长最后把小孩送到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院承诺不留档作强制戒断,但事实表明那地方治不了,还会给患者带来其他不利影响。”
河源的大山成为他们最后的希望。12月中旬是罗全他们计划的新房入住时间,罗伟将迎来目前呆在精神病院的病友。至少在深山里呆两年是家长们的共识,至于小孩自己的想法,以及众多小孩呆在一起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现在顾不上。
罗伟随时都想回去,可是城市环境的诱惑,让他和家人望而却步,罗全认为起码让他再呆一年:“好不容易戒掉了,回到深圳又开始喝怎么办?”已经摆脱了身理上的依赖,可是心里的恶魔可能还会跑出来。
对此疑问,罗伟也不敢打包票:“如果你问我回去还会不会喝。那我只能告诉你,大概有七成把握不喝吧。”
难以克服的“心瘾”
“贩卖点就在我家门口,每天出门都要经过,能忍三个月就不错了。如果我能在远离止咳水的地方循规蹈矩过一年,我就有勇气回家。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这里有问题。”李东指向心脏位置。
与世隔绝始终只是权宜之计,回去还会不会再喝?罗伟也没有把握。身瘾易戒,心瘾难治。
对于自己的未来,罗伟自感一片黑暗,学历不高,没办法找到好的工作,之前的工作经历,都是家里介绍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家里不缺钱,没有什么责任,每天无所事事,根本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心理。”
罗全希望儿子返回深圳后继续工作,然后娶个媳妇。
这是罗伟想要的生活吗?罗伟告诉南都记者,他并不想做回原来的工作:“靠家里人给钱,觉得就像个女人一样,没什么意思。在这里虽然没工资拿,但是也是做事。人还是有点事做比较好。”
具体要做什么罗伟还没有计划,一些内心的想法似乎埋在他心里,他说自己从未和父母谈过自己的理想,他自感沟通是家庭生活中被忽略的一面。
26岁的李东也是深圳的止咳药水成瘾者,目前在广州某机构进行综合戒瘾治疗。他对环境隔离的戒瘾方法也持有赞同态度。“贩卖点就在我家门口,每天出门都要经过,能忍三个月就不错了。如果我能在远离止咳水的地方循规蹈矩过一年,我就有勇气回家。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这里有问题。”李东指向心脏位置。
李东说,要戒掉止咳水,很重要的一点是心里要想清楚‘我回来干什么’?每天24小时怎么分配?这几天他在慢慢想,以前自己是踢足球的,踢得还不赖,为什么不踢足球呢?姑姑家旁边就有足球场,每天下班可以踢一下。
“这几天想的,说的,笑的,比我过去一年时间的都多。”除了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李东最迫切的想法是搞好自己的小家庭,“从9岁起,我就没有家庭的群体生活了,出去后首先要对小家庭负责,把唾手可得的小事做好。”
(文中患者和其亲友均为化名)
声音
为什么喝止咳水?
像我们这样的差学校,这东西很泛滥,一个班20个同学全是男孩子,只有6、7个人不碰(止咳药水)。老师也不管,每天不用读书,无所事事。
——罗伟
成瘾了会怎样?
成瘾后就完全变了个人,脾气非常暴躁,经常变着法子要钱,不给钱,他就动手打人,有一回竟然上来掐住我的脖子,可怕得像魔鬼一样。
——陈玲
怎样戒断“毒瘾”
医院治疗无效,戒毒所不收,就算收了也要留案底,前些天送到东莞一精神病院了,不指望能戒断,希望情况好转时接到河源(大山里)。
——陈玲
话你知
止咳水有多毒?
止咳药水,医用处方药物,因其含有磷酸可待因、盐酸麻黄碱等与毒品相同的成分,容易使过量服用者上瘾。该药品已经被国家列为药物滥用中的一种,有的人甚至称它为“软毒品”。
止咳药水成瘾可以导致口腔粘膜、牙齿的病理改变,肠胃功能受损,肝脏、肠胃、心血管的损害。长期滥用会还对大脑造成损害,导致智力减退和个性改变。
《2007全国年药物滥用监测报告书》显示,对珠三角8所初、高中学校及职业中学的874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滥用“止咳水”者占总人数的11.2%(非医疗目的滥用)。
目前,滥用的止咳药水的品牌从开始主要为联邦止咳露,发展到立健亭、可非、佩夫人多种品牌。因主要品牌而得名,止咳药水上瘾者有一个统称叫“邦友”,文中罗伟等“邦友”能买到的止咳药水主要有一种非法生产经营的假冒止咳药水,它不在药店而是在士多、牛杂店销售,磷酸可待因不再是主要成分,直接加了海洛因或K粉等。禁毒工作人士表示,青少年手中的止咳药水已经是准毒品,更易成瘾,更难戒断,价格也从20-30元飙升到120元/瓶。
新闻链接
向网吧歌舞厅售止咳水
获利逾5000万判监12年
今年6月14日上午,全国首宗对非法销售止咳水定罪的案件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向网吧歌舞厅售卖止咳药水获利5760万元,深圳新天地药业负责人蔡义坚被判12年有期徒刑,罚金20万元。
2010年8月9日,深圳市药监局突击检查罗湖区梅园的一个仓库,发现该仓库非法储存止咳水4000箱,货值金额700余万元,货主新天地公司无法说明这些止咳水的销售去向。
4000箱止咳水合共4.8万瓶,而当年广东省全年正常渠道使用的止咳药水才5万瓶,这批止咳药水几可以满足全省一年用药量。
该案件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成立了由市禁毒办牵头,药监、公安、国税等部门组成的“新天地专案组”,被确定为深圳药品领域三打两建工作的必须侦破和查处的重大案件。
据专案组调查,自2006年起,新天地公司利用其《药品经营许可证》,分别从河北、四川、浙江、江苏四省的多家药品经销商处购进止咳水46万余瓶,货值共计5765.6万元。购入止咳水后,新天地未按照规定进行验收入库,而是秘密藏于临时租赁仓库,然后将止咳水通过非法渠道销售给无药品经营、使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使止咳水从地下渠道流入社会,危害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新天地公司被查处,重击了整个深圳止咳药水销售的地下网络,当年地下市场止咳药水曾一度断货。
采写:南都记者 项男 黄丹
摄影:南都记者 黄丹
富二代喝止咳水上瘾 父母深山建房圈禁逼其戒毒

饭后,罗伟在农舍门前点燃了一支烟。

河源深山里,罗伟住了8个月的农舍。

面对止咳药水的诱惑,24岁的罗伟无法抵挡。父母将他丢入河源农村9个月的隔离,让他逐渐摆脱成瘾的梦魇。这样的自救也吸引了不少深圳成瘾者家庭效仿。与世隔绝始终是权宜之计,回去还会不会再喝?罗伟也没有把握。身瘾易戒,心瘾难治。
被隔离的青年
“割草、喂鱼、扫地还有浇菜。”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在山里的生活,由于甚少与外界联系,罗伟的手机坏了都懒得去修。
24岁的罗伟,拥有让很多同龄人艳羡的身份:深圳原住民、富二代。依靠收租,他所在的家庭拥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
但罗伟已经在河源的偏远村落的一栋危房里生活了九个月。他被父母圈禁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目的只有一个,远离止咳水。
罗伟现在的生活简单而枯燥。早上8点,罗伟的一天从割几十斤鱼草开始。之后,他还要花几个小时,给自己种的青菜浇水,然后打扫舅舅家的房间和走廊。如果有空,他喜欢到附近的村民家里坐坐,聊聊天喝喝酒。晚上,他也偶尔看电视,但更多时候是晚上10点就睡觉了。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罗伟,从未干过此等粗活。“割草、喂鱼、扫地还有浇菜。”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在山里的生活,由于甚少与外界联系,罗伟的手机坏了都懒得去修。
他有些习惯现在的简单生活,但对于回到不算遥远的深圳,他依然流露出向往。没有父母的许可,他寸步难行,即使到最近的县城,也需要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更重要的是,村里的长辈对他严格看管。
罗伟是深圳这座城市改革发展受益最大的“深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在学生时代,他每月都能获得数千元的零花钱。但不幸的是,罗伟沾上了坏习气,恋上了止咳水,在致瘾最深的时段,他每天能喝掉十瓶止咳水。
由于止咳水含有的化学成分,能刺激中枢神经,一次大剂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在深圳,一些年轻人滥饮止咳水的现象一直存在。
据罗伟回忆,他第一次接触止咳药水,是在深圳读中专时,他将沾染恶习的原因归结于所处的环境:“像我们这样的差学校,这东西很泛滥,一个班20个同学全是男孩子,只有6、7个人不碰(止咳药水)。老师也不管,每天不用读书,无所事事。”那一年他14岁,在此后的10年时间,止咳药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那间售卖止咳水的小店,就在他上学、放学的半路上,他承认,十年间自己无数次试图戒“水”,但自己抵抗诱惑的能力太差。
喝得最厉害的时候,罗伟一天就要喝掉10瓶咳嗽水,通常的剂量是一口半瓶。为了缓解喝止咳水之后的口渴,他每天还要喝掉5到6瓶1 .2升的可乐。由于水肿,身高1.6米的他,一度体重飙升到170斤。
邻居看不惯,”他们会和罗伟的父母说‘你儿子好像不太听话’,这句话已经说明了很多。”罗伟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街坊的批评,给父母以及自己很大的压力,感觉自己在社区就是个瘾君子。
深感这样下去不行的罗伟和家人,开始寻找新的解决的方法。
家长的救赎行动
面对逐步好转的儿子,不差钱的罗全,又有了升级版的隔离计划:在山林的更深处盖一栋小平房,专门给儿子用作隔离屋,让儿子在此再调养一年。
钱就在口袋里,药水就在小店里,脱离不了环境,要戒瘾似无可能。
2011年的中秋节,忍无可忍的罗全,终于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救儿子:几天后,罗伟被送到河源农村,一个距离最近县城也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两个小时步行山路的小村落。
这里是一处罗伟舅舅承包的山林,蜿蜒曲折的山路阻止了外界的喧嚣,少有人为开发。尽管珠三角发展日新月异,但这片山林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模样。罗伟居住的小平房,还是上世纪60年代知青修建的瓦房。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罗伟的父亲罗全对记者说,这个地方他很满意:“他买不到止咳药水。”
刚开始的时候,罗伟并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开始的三四个月觉得很不适应,身体和心理的都有。那段时间老是发脾气。”
在此期间,不堪寂寞的罗伟曾经回深圳住了三个多月,很快,自认无法摆脱“心瘾”的罗伟,在半被迫半自愿的情况下再次回到这个远离城市的深山老林里。
山里没有多少劳作事,罗伟也不需要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但舅舅定下了强制性的规定,在罗伟眼中,舅舅是一个强势的人。
“比较懒,不干事,骂啊,不骂不行。”叶伟华这样评价自己的外甥:“要经常说他,跟他讲人生道理,总之在这就不能给他主动权了。”谈话中,叶伟华避着止咳药水四个字,以“那东西”指代,认为不是什么好东西。
经过9个月的隔离生活,让罗伟的身体状况好了很多,170斤体重减到了130斤,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一边是亲人热心安置,另一边是要早点跑出去的心。“在山里8个月,我想回去,其实我每一天都想回深圳。”罗伟没有跟父亲提起过这种想法。
面对逐步好转的儿子,不差钱的罗全又有了升级版的隔离计划:在山林的更深处盖一栋小平房,专门给儿子用作隔离屋,让儿子在此再调养一年。
对于罗全的计划,靠近这个家庭的另外一个家庭也非常感兴趣,已明确表示要参与进来,这个家庭的一个年轻人,同样深陷止咳药水之瘾不能自拔。
在河源市连平县元善镇的深山里建一所房子,让罗伟在山里至少再住上一到两年,这样的房子大约花费30万。这对于罗伟家族来说,钱完全不是问题。据记者了解,这个家族属深圳原住民,在城市核心区拥有大量出租屋,用罗伟的话说,只要不胡乱挥霍,父母攒下的积蓄,所有家庭成员一辈子都花不完。
10月30日上午,罗全驱车四小时来到连平县元善镇仙塘下林场,午饭后,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山路进山选定了建房子的地点。“不要建得太好,但一定要快,最好12月就能住上。”
8是个吉利数字,但11月8日皇历显示“诸事不宜”,罗全选择11月7日破土动工建房子。
无论是选址半山腰盖房子,还是去留问题,罗伟都没有任何发言权,他悄悄对记者说,自己不想呆在山里。
罗伟要了根烟,蹲在一边看着父亲和叶伟华忙碌地指挥工人。砂石、钢筋和水泥都齐备了,加上当地高效率的师傅和小工,眼前这个专门为自己建的房子在12月中旬就可以完工了。